两年前,我读到《联合报》的一篇报导《平溪东势格-日据老桥拚观光》,介绍了台北县平溪乡的“东势格古道”。 看到标题时,以为大概是是介绍东势格派出所前的那一座日据老桥,以及我所熟 悉的“东势格越岭古道”。
读完整篇报导,才发现它指的不是我认知的古桥及古道,更令人惊奇的是,这篇报导提到这条古道上, 有光绪元年(1875)的古老土地公庙,沿途有七、八座古桥,而且古道两端都是日据时代兴建的石桥, 分别命名为“万寿桥”、“长亨桥”。其中长亨桥保存最为完整,桥边的石碑刻着捐钱造桥 者的姓名,而石碑的两侧有后人加刻民国四十二年(1953)的字迹以及国民党的党徽。
光凭这样的叙述,古桥、古碑及古老的土地公庙,足以让古道爱好者看了直流口水吧!不过这篇报导 却没提到“东势格古道”的确切位置。当时随即上网块寻,用尽了这篇新闻报导所有特殊的 关键字,例如“万寿桥”、“长亨桥”、“光绪元年土地公庙”、“平溪东势格”等,用各种交叉 组合查询,却没找到任何相关的登山记录。
后来心想,或许是这条古道才刚曝光,过一阵子应会有山友的探访记录。没想到,后来上网查询,仍然 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资料。心里觉得纳闷,拥有七、八座古桥的古道,已极为罕见,而且这条古道 位于登山客及单车族经常出入的平溪东势格,又经媒体报导,怎么事后没有任何相关的网志记录呢? 颇让人纳闷。于是继续等待,而时间一久,竟渐忘此事。
图:紫东产业道路(北43乡道)通往竿蓁坑
最近查询登山资料时,无意间得知,今年五月台北县政府将台北县平溪乡的“竿蓁坑古道”登录为文化景观。 古道被登录为文化景观,是相当罕见的情形,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
更离奇的是,我在台北登山旅行多年,已走过不少古道,我竟然不曾听过平溪乡有一条“竿蓁坑古道”。 根据台北县文化局的公报所述,竿蓁坑古道的范围:“自万载桥本体至长亨桥本体 古道(含土地公庙、古碑及石田部长纪念碑遗址)。”
竿蓁坑古道被登录为文化景观的理由如下:(转载自县政府公报)
一.平溪乡竿蓁坑古道系昔日平溪地区居民联系坪林的主要道路,留存先民的产业交通发展、
聚落开发历史记忆,于地方发展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态休闲、乡土教育等均具保存之价值。
二.古道位于平溪乡竿蓁坑聚落内保存完整的古老土地公庙与石碑,沿途亦有长亨、万载两座保存尚完整的
石板桥、老榕树,以及日治时期石田部长纪念碑遗址,深具平溪地方先民拓垦的历史见证意义。
看到这则资料,我立即明白,两年前看到的“东势格古道”新闻报导,指的就是“竿蓁坑古道”, 如今已被县政府登录为文化景观。如此一来,我的心情就跃跃欲试了。竿蓁坑, 位于平溪东势格往坪林的紫东产业道路(北43乡道)上。我虽然并不晓得竿蓁坑古道的确切位置, 但心想既然古道已被列为文化景观,则向当地人探询,应该不难查知。于是选定今天前来平溪,爬完山, 回程时,前往竿蓁坑寻访这条古道。
从106公路岭脚与望古之间的“白莺桥”旁,转入紫来产业道路(北43乡道),前往东势格。车行约3公里, 来到东势格派出所前的叉路,取右行,为通往坪林的紫东产业道路。
过了东势格派出所,就放慢了车速,留意沿途有无“竿蓁坑古道”的标志或土地公庙的身影。 慢速前行了一公里多,却一无所获,而沿途冷清,没有人车经过。
图:光绪元年土地公庙-张福宫
这时,从后照镜看见一辆警车从后面驶来。我赶紧停车,摇下车窗,警车经过时,停在我车旁,员警也摇下车窗, 好奇询问我在这里做什么。原来这是东势格派出所的巡逻车。
我说明来意,于是并排停车,隔着车窗对谈起来。拿资料问这位警察先生, 他却回答说,没听过长亨桥、石田部长纪念碑,也不知道光绪元年的土地公庙在哪里。 是竿蓁坑了。
他说,前面不远处的路旁是有一座土地公庙,不过庙还蛮新的。聊了一下,他就先开车走了, 继续他的山区巡逻任务。我休息了一下,才开车前进。
来到紫东产业道路5K附近,果然看见右侧路旁有一间土地公庙,而那辆警车也停在这里。下了车, 看见刚才那位员警,正俯身查看土地公庙。看见我走过来,他回头说:“没看见光绪元年的字迹。” 原来他也好奇而热心的帮忙找寻。我趋近查看,是一座石砌的土地公庙,庙名为“张福宫”, 庙身抹上红漆,也增建新式的供桌及拜亭,心想应该不会是光绪元年那座土地公庙。
正感到失望之际,这位员警移动身体,我突然瞥见庙旁的角落竟有一块古碑。趋前查看,石碑的起句 刻着“光绪元年”,大喜过望。这位员警也蹲身查看,果然是警察本色,他说石碑捐款者很多姓杨, 现在竿蓁坑这一带也是以杨姓居民为主。知道古碑就座落于路旁,他有点担心古碑会被宵小偷走。
与这位热心的员警再次道别,他先离去,继续执勤。土地公庙旁有条小径通往溪谷,这就是竿蓁坑古道了。 入口旁的树上挂着许多的登山条,不过不是因为这条古道的缘故,而是土地公庙旁的树下有一颗矿 务课No.178基石。山友来此探访基石,却浑然不知基石旁的小径就是竿蓁坑古道了。而平溪乡公所 又为何不竖立告示标志呢?
|
|
|
| 警车停在张福宫前,左前方叉路口有紫云宫标志。 | 光绪元年的捐建古碑。 |
图:竿蓁坑古道上的古桥
往下走,山径随即与一条横向的山路交会,山径直下溪边,而这条横向的山路,就是竿蓁坑古道了。 先取左行探路。山路宽阔平缓,位于林荫,充满古道气氛,而古道就在公路下方,与公路平行。
带着惊喜的心情前进,没想到才走约百公尺,古道就接回公路。古道竟然这么简短, 于是循原路折返,改探右路,看看另一端的古道路段通往何处。往另一端走,前行几十公尺, 前方出现一座古桥。
这古桥的景象令人震撼,由石板铺成的古桥跨越竿蓁坑溪的支流,这里因地形剧烈落差而 形成小峡谷,古桥与溪谷相距约三层楼高,古桥已无护栏,走在桥面,心情惶惶不安。 附近地形狭窄,找不到适当位置取景,以拍出这峻谷险桥的画面。
这座古桥并无任何刻字,是否是“长亨”、“万载”(或万寿)桥之一呢?或只是古道七、 八座古桥之一呢?桥的另一头被野生的竹丛挡住,周遭杂草横生,已无去路。
这时感到纳闷,竿蓁坑古道就只剩这么短短一、两百公尺而已。那有民国四十二年及国民党的党徽 刻字图案的长亨桥在哪里呢?而石田部长纪念碑又在何处呢?
回到张福宫,决定开车续往上行,沿途再搜寻看看。前行不远,左侧有间古朴的石头厝(竿蓁坑17号), 停车拍照后,续行。一路却无所获。心想再继续前进,就通往坪林了。于是决定折返,前往东势格派出所寻求协助。
图:长亨桥
来到东势格派出所,遇见了刚才那位员警,他已巡逻完毕,回到派出所。派出所内员警好奇靠拢过来讨论, 却没人知道石田部长纪念碑、长亨桥在哪里。我想到或许可询问当地的文史工作者,这时一名资深员警 立即说,他可帮我打电话询问。他拿起电话拨号,不久,就问到消息了。
这位员警转述说,从张福宫再往前走不远,路旁有一间石头厝,长亨桥就在附近。我问:“石头厝 是不是竿蓁坑17号?”果然就是我刚才停车拍照的古厝。古厝的前面有小径可通往溪谷。 员警说,长亨桥、石田部长纪念碑就在那附近。
来回奔波,辛苦询问,终于得到美好的回报。于是驱车回到竿蓁坑17号石厝处。石厝对面路旁有条小 径通往溪谷。走下小径,发现这里已铺设了新颖的水泥石阶路,朝右下方,通往溪边。来到溪谷, 却只见一座新建的水泥桥跨越溪谷。古桥在哪里呢?过桥,水泥石阶路通往附近山坡一间农寮及农圃而已。
折回到小径入口,这时才发现野姜花旁另有一条小径,通往左下方溪边。进入一探,竟是柳暗花明, 出现了一条平缓的山路。且惊且喜的往前走,没多久,一座古桥就出现在我面前了。
这座古桥的规模更大,由两座石砌桥墩为支挡,桥面由三段长石板衔接而成,每段桥面约有七或八根长石 桥并排。桥面的护栏亦由石板砌造,但只剩部份残杆而已。过石桥,查看桥柱,写着“长亨桥”三个大字。 我终于找到长亨桥了。
图:长亨桥桥柱的刻字
赶紧查看桥柱柱面,是否有民国四十二年的刻字及国民党党徽?但见石块磨损斑驳, 纹痕似字又非似字,模糊难辨。用手指触摸,石面凹凸纹路仿佛像是国民党党徽的 十二道白日光芒,果真是吗?我也有点怀疑。
再查其它石柱,却找不到类似党徽的图案。这时,自己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 渴望看见国民党的党徽吧!
往回走到桥的这头,抬头时却蓦然发现在山壁草丛处立着一块长方形的石碑, 这才突然会意过来。刚才看见古桥时,竟因过度兴奋,而忘了资料提到,民国四十二年的刻字 及国民党党党徽是刻在石碑上,而不是在古桥的桥柱。
果然石碑中央上方,刻着明显的国民党的党徽,但雕刻粗略,青天白日只有九道光芒而已。党徽下横刻着 “万载长亨两桥”几个大字。石碑中间则有密麻的捐钱修桥者的姓名。右侧有“民国四十二年…” 的刻字,左侧则有“岁次辛卯…”等字,字迹都有点模糊了。
长享桥找到了,而万载桥呢?当年新闻报导所提的“万寿桥”,可能就是指“万载桥”。万载桥在哪呢? 是不是张福宫附近深谷上的那座古桥呢?还是这附近还有古桥?
过了长亨桥,续行探路,爬上一小段古朴的石阶,来到一片茶园。古道至此,路径完全消失,周围 茶园找不到任何去路。只好又折返回长亨桥。站在桥上,俯瞰桥下流水,心里还想着,石田部长纪念碑又在哪里呢?
长亨桥附近的这一段竿蓁坑古道,长度大约也只有一、两百公尺而已。仅存的古道只有一小段, 古桥孤然隐身于这幽静的淙水岸间。站在古桥上,我心头却有有强烈的感动。
是这里的风景美得令人感动吗?不是。是因为国民党的党徽吗?当然不是。 是一股浓郁的古道气氛,盈绕在我的周遭。这无色无味的古道气氛,却难用文字形容或叙述,只能在现场感受。 面桥的石板,桥柱的青苔,桥畔的古碑,桥下的流水,桥边的芒花,茶园的茶香,古道的落叶,与旅人的情怀, 共同谱出这扣人心弦的古道气氛。
而石田部长纪念碑究竟在哪里?我在附近没有找到。这石碑应是纪念一位日本人,而我始终无法搜寻 到关于他的事迹。这要祈盼东势格的地方父老及文史工作前辈们来指点迷津了(注1)。
旅游日期:2009.11.04
【相关标签】
注1:
回到台北后,继续搜寻关于石田部长的资料。这次竿蓁坑古道之行,多知道了一个关键字,
光绪元年这座古老土地公庙的名字-“张福宫”。
用google搜寻“张福宫”,竟然一下子就中“宾果”了。说来有趣, 我熟识的山友Jennifer(字恋姐)在六年前写过一篇《东势格寻幽记》。她在旅记中提及:
“依陈奶奶的指示,车行仍是走上43线乡道往坪林的方向前进,经过“芊蓁坑2号”
民宅前算是遥远的距离时,道路右侧建有一妆饰华丽的土地公庙,据陈奶奶告知:
此一土地公庙于古早的清朝时代即已存在着。过土地公庙后,雨已暂停、
向晚的冬阳也露脸了!此时“芊蓁坑 17号”的土角厝终于出现在我眼前。…””
“于庙前方的马路旁边,发现立有一矿物课178号的基石,其对面的木制电线杆上是标示“芊蓁高分63”。
陈奶奶并叙及,她尚是年幼时,土地公庙前方约是此电线杆的下方处,曾有一日本人殉职
的纪念碑竖立着;日据时代,日本人经常携小学生来此祭拜。光复后,她都还曾见过,惟因其不识字,
也不知碑文是纪念何种样丰功伟业的日本人,后来此纪念碑究流落何处去,已无从查考了!”
《东势格寻幽记》的网址: http://www.yougoipay.com/jennifer/Travels1/t38.htm
【后记】
●“竿蓁坑”,或写作“芊蓁坑”,当地的门牌使用“芊蓁坑”一词,但有的公告标志也用“竿蓁坑”,
台北县文化局的公告使用“竿蓁坑古道”,所以本文相关地名叙述一律使用“竿蓁坑”。
根据学者考证,“竿蓁坑”才是正确用法。竿蓁,与闽南语“肝真”读音相同,
是指台湾原生的一种类似五节芒的茅草。台湾各地都有竿蓁地名,
以台北县为例,淡水镇有“芊蓁林”,双溪乡有“千蓁林”等。学者认为,竿蓁的古字为
“菅蓁”,由于早期来台的移民识字有限,地名大多先有语音,后来才套用读音相近的文字,
因此产生“竿蓁”、“芊蓁”、“千蓁”等不同的地名,但其读音相同,都读为“肝真”(台语)。
●关于石碑上“民国四十二年”的刻字,后来我进一步查询发现,岁次“辛卯”应为民国四十年。
再仔细对照所拍的石碑照片,发现刻字应为“民国四十年十二月”,
可能是当时新闻报导有误,或者因为石碑刻字模糊,地方人士误认为是民国四十二年。
图:长亨桥石碑-“中华民国四十年及国民党党徽”是否为后人添刻?
●关于石碑上的国民党党徽及“民国四十年”刻字,被认为是后人添刻的,此事或许曾向当地耆老求证过,
我则有一些疑点,希望能向当地文史工作者再求证。或许党徽及民国四十年并非后人添刻的。我的理由如下:
一.我曾在别的古道看过类似的石砌古桥,当时先入为主的印象,都认为这种古朴的石桥应是日据时代兴建的,
却发现桥头或桥旁的石碑年代是民国四十几年。由此可见,这座古桥亦有可能是民国四十年(1951)重新修造的。
二.若长亨桥是日据时代兴建的,则石碑上应该会有日本纪元(如明治、大正、昭和)等。而一般常见的情况是,
这些日本纪元会被后人涂销(例如东势格派出所前的东势格古桥昭和刻字),很少会另外添刻中华民国纪元。
这块长亨桥石碑却完全看不到有日本纪元或被涂抹的痕迹。此外,石碑左右侧刻的“民国四十年”及“岁次辛卯”字迹都很大,
可能是原石碑已预留空间来刻这文字,若是后人所添刻,则原来的日本纪元痕迹在何处?石碑又如何先预留
左右空间让后人添增这些文字呢?
三.另外一个证据是,“民国四十年”、“岁次辛卯”刻字与石碑大标题“万载长亨两桥”的字体及刻工
极相似,应是同一时期所为,则这座桥可能也是民国四十年所建的。
或许这座长享桥就是兴建于民国四十年。以上只是我个人猜测,提供个人观察到的疑点,并无翻案之意。
最后,还有一个个人主观的看法。我曾见过不少日据时代的古桥,桥名通常采用当地的地名,或者选
用字义较通俗浅明的文字做为桥名。“万载”、“长亨”读起来则感觉比较像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时的心情用语。
[旅行照片]
[旅行地图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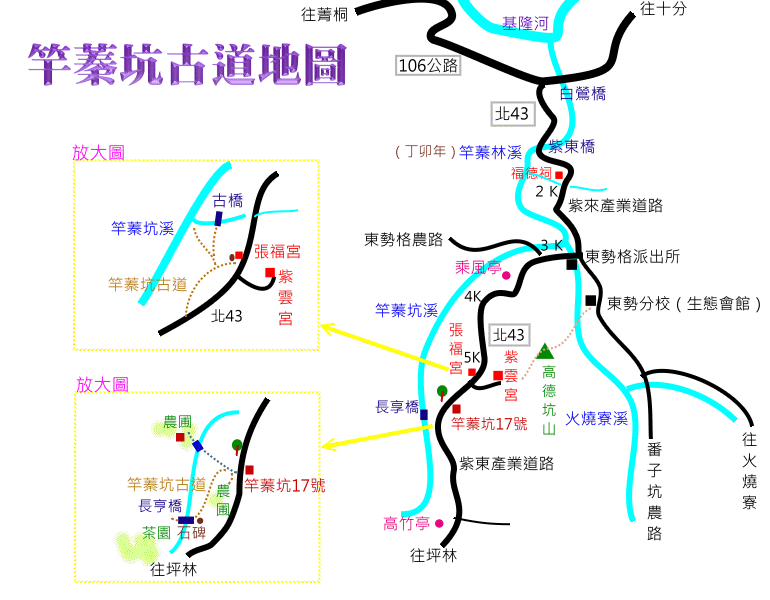
|
[交通地图](可用箭头上下左右移动及放大缩小)
在较大的地图上查看竿蓁坑古道
●如何前往光绪元年张福宫及长亨桥?
从国道五号下石碇交流道,沿106公路往平溪乡,至岭脚与望古之间的“白莺桥”旁,右
转入紫来产业道路(北43乡道),至东势格派出所前叉路,右转紫东产业道(仍为北43乡道),
约至5K处,即可看见右侧路旁的张福宫,前方左侧叉路口有紫云宫的标志。续行北43乡道,
不远处,即可看见竿蓁坑17号石头厝。对面马路有小径通往溪谷,取左行,即可前往长亨桥。